几天后,永安村农会在晒谷场召开大会,准备正式成立农军自卫队,由谭统南担任队长,谭先民担任副队长。附近几个村的贫苦农民来了数百人,场面热烈。
谭统南站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激昂地宣讲着成立农军的意义:“乡亲们!我们有了自己的枪杆子,地主老财就不敢再随意欺压我们!我们要保卫我们的粮食,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农会斗争的成果!”
台下群情激奋,“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谭睿和谭统华站在人群前列,同样心潮澎湃。谭睿知道,这是东兰农民运动走向武装斗争的重要一步。
就在这时,异变陡生!晒谷场四周突然响起了尖锐的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大批身着统一黑色短褂、手持快枪、大刀、长矛的武装团丁,在一个骑着高头大马、面色阴鸷的中年汉子带领下,包围了晒谷场。
是地主覃福满!他竟然亲自带着他的民团来了。
“谭统南!你们聚众造反,私设武装,攻击乡绅,罪大恶极!今天本团总就要替政府剿灭你们这群乱党!”覃福满坐在马上,用马鞭指着台上的谭统南,声音冰冷而嚣张。
场下的农民们一阵骚动,有些胆小的已经开始往后缩。他们手里的锄头、粪叉,在团丁明晃晃的快枪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谭统南临危不乱,站在台前,厉声喝道:“覃福满,我们农会依法成立,维护的是贫苦农民的利益!你带着武装团丁冲击农会集会,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哼!牙尖嘴利!给我拿下谭统南,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覃福满失去了耐心,直接下令。
“保护主任!”谭先民大吼一声,第一个冲上前,举起手中的梭镖。谭统华眼疾手快,一把将身边的谭睿推向谷堆后面,自己则像灵猫一样矮身蹿出,手中弹弓连发,两颗石子精准地打在冲在最前面两个团丁的脸上,打得他们嗷嗷惨叫。
“砰!”
一声枪响划破喧嚣。
是覃福满开的枪!子弹打在谭统南脚下的木台上,木屑纷飞。
“谁敢动!”覃福满举着还在冒烟的驳壳枪,杀气腾腾。
这一枪,彻底点燃了冲突的导火索。农会成员们被激怒了,压抑已久的怒火爆发出来。
“跟他们拼了!”
“保护农会!”
农民们挥舞着简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团丁混战在一起。晒谷场上顿时刀光剑影,喊杀声、惨叫声、枪声响成一片。
这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团丁有备而来,武器精良。农会成员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训练和有效武器,不断有人受伤倒下。
谭睿躲在谷堆后,看着这血腥而残酷的一幕,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他看到谭先民挥舞着梭镖,勇不可挡,接连刺伤了两名团丁,但很快就被几把长矛逼得连连后退,胳膊上被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袖。
他看到谭统南被几个团丁围住,他手持一把夺来的大刀,奋力劈砍,身形矫健,但险象环生。
他看到谭统华利用身材矮小的优势,在人群中穿梭,不时用弹弓、石块甚至撒泥土干扰团丁,帮农会成员解围。
混乱中,覃福满带着两个心腹,狞笑着朝谭统南背后摸去,手里举起了砍刀。
“太爷爷!小心背后!”谭睿看得真切,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大喊出来。
谭统南闻声猛地一侧身,覃福满的砍刀擦着他的肩膀落下,砍破了衣服。谭统南反手一刀,逼退了覃福满。
正在这时,他正面露出破绽,一个团丁挺枪便刺!
“大哥!”
千钧一发之际,谭统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猛地将谭统南推开,自己却没能完全躲开,那长矛的尖锋狠狠刺入了他的大腿!
“统华!”谭统南目眦欲裂。
谭统华闷哼一声,摔倒在地,鲜血迅速从裤腿渗出。
“小弟!”谭统南像发怒的雄狮,刀法变得更加狂暴,暂时逼退了周围的团丁,扑到谭统华身边。
农会成员见领导人受伤,更加愤怒,但也更加混乱。眼看伤亡越来越大,情况万分危急。
“呜——呜——呜——”
就在这时,远处山路上传来了低沉而雄浑的牛角号声!紧接着,是震天动地的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农会兄弟们顶住!武篆援兵到了!”
“打倒反动民团!”
只见山坡上,无数火把如同火龙,成百上千的农军战士,在李明瑞和几名骨干的带领下,手持各种武器,如同潮水般涌来。他们得到了谭睿之前暗中让一个腿脚快的孩子送去的情报。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呀。
覃福满的民团见状,顿时慌了手脚。他们没想到农会的援军来得这么快,人数如此之多。
“撤!快撤!”覃福满脸色剧变,调转马头就想跑。
“哪里走!”李明瑞一马当先,抬手一枪,打中了覃福满坐骑的后腿。马匹惨嘶一声,将覃福满掀下马来。
团丁们见头领落马,顿时作鸟兽散,丢下武器抱头鼠窜。农军乘胜追击,俘虏了不少团丁。
晒谷场上的战斗很快结束,留下了斑斑血迹和痛苦的呻吟。农会虽然取得了胜利,打退了民团的进攻,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人受伤,谭统华伤势最重。
谭统南抱着血流不止、脸色苍白的谭统华,声音哽咽:“小弟!撑住!你一定要撑住!”
谭睿看着眼前惨烈的一幕,看着小太爷爷腿上那个狰狞的血洞,心中充满了悲愤和历史沉重的实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真的会流血,会牺牲的。
谭统华的伤势很重,矛头几乎刺穿了大腿,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普通的草药已无能为力。
“必须马上找西医!不然这条腿保不住,人也危险!”李明瑞检查伤势后,沉痛地说。
然而,坡峨街上的诊所被覃福满的人盯着,去县城路途遥远且不安全。
“我知道一个人。”谭先民忍着胳膊的剧痛说,“弄京山那边有个传教士医生,叫约翰,是美国人,但为人善良,经常给穷人看病,不问来历。只是……那里是深山,路很难走,而且传闻有瘴气。”
“管不了那么多了!”谭统南毫不犹豫,“就去那里!我背他去!”
“大哥,你目标太大,民团肯定在到处搜捕你。我去!”一个声音响起,是谭统南忠厚但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五弟——谭彩华。
“不,我和谭睿去。”谭统南看着谭睿,“你读过书,可能会说几句洋文,沟通方便。而且你身份不明显,不容易引起注意。”
谭睿重重点头。他深知,小太爷爷绝不能在这里倒下,历史还需要他走下去。
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艰难跋涉开始了。由谭彩华带路,谭睿和另一名精壮农会成员用临时制作的担架抬着昏迷的谭统华,冒着淅淅沥沥的山雨,钻入了云雾缭绕、野兽出没的弄京深山。
山路泥泞湿滑,荆棘密布。谭睿的肩膀很快被磨破,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他咬着牙,和同伴一起,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担架的平衡。谭彩华在前面用柴刀开路,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深山老林,古木参天,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腐烂树叶和湿土的气息,偶尔传来不知名野兽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所谓的“瘴气”,更像是原始森林中动植物腐败产生的有毒气体,让他们感到头晕、胸闷。
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了民团搜索的痕迹。附近的地主民团好像知道了他们要从这里级过,不肯罢休,派出了小股队伍进山搜捕。
有一次,他们几乎与一队五六人的团丁迎头撞上。幸好谭彩华耳朵灵光,提前听到了动静,几人迅速躲进一个狭窄的山洞,用藤蔓遮住洞口,屏住呼吸,听着团丁的咒骂和脚步声从洞外经过,心脏都快跳到了嗓子眼。
担架上的谭统华时而昏迷,时而因高烧和疼痛发出模糊的呓语:“大哥……快走……别管我……”
谭睿握着他滚烫的手,低声安慰:“小太爷爷,坚持住,就快到了。”
经过一天几乎不眠不休的艰难行军,他们终于在天黑时分,根据谭先民画的简陋地图,找到了隐藏在山谷溪流边的一座简陋木屋。木屋前挂着一个小小的红十字标志。
开门的是一位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约莫四十岁左右的西方男子,正是传教士医生约翰。他看到担架上伤势严重的谭统华和疲惫不堪、满身泥泞的谭睿等人,立刻明白了过来,没有多问,用生硬的当地话说道:“快,抬进来!”
木屋里散发着消毒水和草药混合的气味。约翰医生动作迅速而专业,他检查了谭统华的伤势,脸色凝重:“感染很严重,需要立刻手术清创,而且他失血太多,需要输血。”
“用我的血!”谭睿和谭彩华几乎同时伸出手臂。
简陋的手术在煤油灯下进行。没有麻药,谭统华在剧痛中醒来又昏死过去。约翰医生额头上满是汗珠,谭睿在一旁充当助手,递器械,按住伤腿,看着医生用手术刀刮去腐肉,清洗伤口,缝合血管……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当伤口被妥善包扎好,约翰医生给谭统华注射了珍贵的消炎针剂后,他才松了口气:“上帝保佑,送来得还算及时。但能否挺过去,还要看他自己的意志力和接下来的恢复。”
这是谭统华生平第一次和美国人接触,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他还要不断和美国人接触,而且一起工作。现在,他是不知道这些的。
谭睿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但呼吸逐渐平稳的谭统华,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巨大的疲惫感袭来,他几乎站立不稳。
约翰医生给他们准备了简单的食物,看着狼吞虎咽的几人,叹了口气:“你们是农会的人吧?我听说过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这条路,太艰难了。”
谭睿望着窗外云雾缭绕的群山,心中默然。是的,艰难,但必须走下去。这次深山求医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革命环境的残酷和先辈们付出的巨大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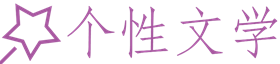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