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九点,陆氏集团顶层一号会议室外。
栖雀在徐特助的引导下,踏出电梯。脚下是触感柔软、能吸收所有噪音的高级定制地毯,走廊宽敞明亮,墙壁是冷色调的金属材质,镶嵌着简洁的线条灯,映照着每一寸空间都纤尘不染,却也带着一种不近人情的、充满秩序感的冰冷。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与高级木质香气混合的味道,那是金钱与权力最直观的味道,也预示着这里并非寻常人可以涉足的禁地。
她今天穿了一身中规中矩的烟灰色套裙,剪裁合体,面料上乘,但样式保守,颜色低调,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脸上化着得体的淡妆。这副打扮,是她对着衣柜挑了许久才决定的——不能太引人注目,不能抢了任何人的风头,要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安静的背景板。她是来“列席”的,不是来“发言”的,更不是来“崭露头角”的。陆聿珩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是一种变相的、放在眼皮底下的观察和考验。
徐特助在厚重的双开檀木门前停下,侧身,朝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表情是一贯的恭敬,眼神里却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探究。“太太,里面请。会议已经开始五分钟。您的位置在最后排,左手边第三个,桌上已为您准备了会议资料和矿泉水。”
栖雀微微颔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丝莫名的悸动,伸手,轻轻推开了厚重的实木门。
门内,是一个与走廊截然不同的世界。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占据了大半个房间,桌体是深色的紫檀木,光可鉴人,折射出顶上天花板垂下的、宛如星辰的水晶吊灯的光芒。桌边已经坐了近二十个人,清一色深色西装,神情严肃,气场沉凝。会议正在进行,投影仪的光束打在正前方的白墙上,映出复杂的财务报表和曲线图,一个头发花白的董事正用沉稳的语调分析着上季度的投资回报率。空气里飘浮着咖啡的微苦气息,键盘敲击声、纸张翻动声、以及低沉的讨论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高压、高效、不容置疑的氛围。
栖雀的出现,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深潭,在会议室里激起了一圈不易察觉的涟漪。虽然每个人都极力掩饰,但那些瞬间投射而来的目光——探究的、好奇的、评估的、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审视与轻视——仍如实质般落在她身上,让她背脊微微绷紧。她甚至能感觉到,有几道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带着评估商品价值般的冰冷打量,然后才若无其事地移开。
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垂着眼睫,脚步放得极轻,像猫一样,沿着墙边走向后排那个唯一空着的位置。她能感觉到,主位上,陆聿珩的目光,在她推门进来的那一刹那,似乎就若有若无地扫了过来,但并未停留,很快就回到了面前的平板电脑上。他今天穿着一身手工定制的深灰色西装,坐在主位,姿态从容,却散发着掌控一切的强大气场。他没有看她,仿佛她的到来,不过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栖雀在指定的位置坐下,面前果然放着一份会议资料和一瓶水。她拿起资料,没有翻开,只是安静地放在腿上,双手交叠,目光落在正前方投影的报表上,表情平静,眼神专注,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来旁听的、努力想融入这个陌生环境的、安静的听众。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她经历过的最漫长、也最需要集中全部精神的三个小时。会议的内容涵盖陆氏集团近期几个核心板块的业务进展、财务数据、风险评估,以及下一季度的战略规划。董事们和高级副总裁们轮流发言,言辞犀利,数据精准,观点交锋激烈,每一个决策背后都牵扯着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资金流动和市场风向。
栖雀坐在后排,像一个最认真的学生,安静地听着,看着。她不发一言,甚至很少翻动手中的资料,只是偶尔拿起矿泉水瓶,小口地抿一下。她的目光大部分时间落在发言者身上,或是前方的投影屏幕,表情始终是平静的,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努力理解的认真,以及掩饰得很好的、对专业术语的茫然。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复杂的财报数据、晦涩的专业名词、瞬息万变的市场分析,是如何在她脑海中自动解构、重组、分析。她能清晰地看到某个海外项目风险评估报告里的逻辑漏洞,能瞬间计算出一组并购数据背后隐藏的杠杆倍数,能本能地判断出某位董事提出的扩张策略隐含的潜在政策风险……这些几乎是她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青鸟”赖以生存的敏锐触觉。可她必须将它们死死压住,用尽全力维持着脸上那副“似懂非懂、强自镇定”的表情。
有好几次,当某位以激进著称的年轻副总提出一个看似前景广阔、实则风险极高的海外收购案时,栖雀的指尖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当另一位保守派董事用过于悲观的数据模型质疑一项新兴科技投资时,她的呼吸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她的表情,始终完美无瑕。她甚至还在听到某个过于专业的缩写术语时,恰到好处地微微蹙了下眉,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困惑。
会议进行到后半程,讨论进入白热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项对东南亚某国新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支持派认为这是抢占未来市场的绝佳机会,反对派则强调当地政局不稳、政策风险过高。双方僵持不下,会议室内气氛有些凝滞。
一直沉默的陆聿珩,目光终于从平板电脑上抬起,缓缓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会议桌末尾,那片阴影与光线的交界处,落在那道安静得几乎要消失的身影上。
“沈栖雀,” 他的声音不高,在略显嘈杂的议论声中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的冷冽,瞬间让会议室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带着惊愕、诧异、玩味,以及毫不掩饰的好奇。她?陆太太?一个从未参与过任何核心事务、看起来怯懦安静的花瓶,在这种级别的会议上被点名?
栖雀的心脏猛地一跳,指尖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她抬起眼,迎上陆聿珩深邃无波的目光,那目光平静得像一片深海,看不出任何情绪,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重量。
“是,陆先生。” 她站起身,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被点名的紧张。
“坐。”陆聿珩言简意赅,目光依旧停留在她脸上,不疾不徐地问,“听了这么久,对刚才讨论的这个新能源项目,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激起千层浪。在座的都是陆氏的核心高层,浸淫商场多年,对如此复杂的跨国投资案尚且意见不一,争论不休。陆聿珩竟然问一个外行?一个据说只是靠着替嫁才坐上陆太太位置的女人?
各种意味不明的目光,瞬间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栖雀身上。有不屑,有嘲讽,有等着看笑话的戏谑,也有少部分人,如徐特助,眼中闪过深思。
栖雀感觉自己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她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这不是沈惊霓那种带着恶意的刁难,这是陆聿珩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陆氏最核心的权力场中,对她发起的一场不动声色、却更为致命的审视。答得太好,会立刻引起他更深的怀疑;答得太差,或者干脆说不出个所以然,坐实“草包”之名,那她之前的种种“灵光一闪”就成了笑话,陆聿珩很可能彻底失去兴趣,将她重新打回“无关紧要”的角落。
她必须回答,而且必须回答得“恰到好处”。
她垂下眼,手指不安地绞在一起,脸上恰到好处地浮起一层薄红,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忐忑和不确定:“我……我不是很懂这些……就是,就是刚才听几位董事讨论,好像……好像都在说那个国家……嗯,政局不太稳?”
她顿了顿,抬起眼,怯生生地看了一眼陆聿珩,又迅速低下头,声音更小,带着一种“不懂就问”的笨拙:“我……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报道,好像说那个国家……新上任的能源部长,背景好像……有点复杂,和当地几个大家族走得很近,而且,他上台后,好像……好像废除了前任的几项新能源补贴政策?”
她的话,断断续续,用词也含糊,甚至带着不确定的“好像”,仿佛只是从什么八卦杂志或者新闻里道听途说来的皮毛。但其中提到的“能源部长背景复杂”、“与当地家族关系密切”、“废除前任补贴政策”,恰恰是刚才争论中,反对派提出的最关键、却也最容易被数据模型忽略的“非商业风险”之一。
会议室内,有几道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支持派的激进副总皱起了眉,反对派的保守董事眼中则闪过一丝意外和深思。
栖雀像是被这些目光吓到了,慌忙摆手:“我……我就是瞎说的,我不懂这些……陆先生,对不起……” 她脸上露出惊慌和懊悔,仿佛为自己的“多嘴”而后悔不迭。
陆聿珩静静地看着她,目光深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没有对她的“看法”做任何评价,只是淡淡地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手中的文件,仿佛刚才的提问只是一时兴起,无足轻重。
“继续。” 他对会议主持人示意。
会议继续进行,仿佛刚才的小插曲从未发生。但会议室里的气氛,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那些或轻视或好奇的目光,在重新投向她时,少了几分戏谑,多了几分审视和掂量。而陆聿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也没有看过她一眼。
直到会议结束,众人陆续离场,栖雀才在座位上,轻轻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的衣衫已经微微汗湿。她最后一个起身,收拾好面前纹丝未动的资料和水瓶,低着头,准备安静地离开。
“太太,请留步。” 徐特助的声音在身侧响起。
栖雀停下脚步,抬头看他。
“陆总请您去办公室一趟。” 徐特助侧身,为她让出通往另一侧专用通道的路。
该来的,终究会来。栖雀的心脏,在胸腔里沉沉地坠了一下。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默默跟上徐特助的脚步。
顶层总裁办公室位于走廊的尽头,占据了整整半层楼的空间,视野极佳,能将大半个海城的繁华尽收眼底。但此刻,栖雀无心欣赏。她走进这间装修风格冷硬简洁、充满男性气息的办公室时,陆聿珩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她,俯瞰着脚下的车水马龙。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为他挺拔的背影镀上一层金边,却并未增添丝毫暖意,反而更显得他身影孤峭,气压低沉。
徐特助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空气里弥漫着顶级雪茄残留的淡淡气息,混合着皮革和纸张的味道,寂静得能听见墙上古董座钟滴答走动的声音。那声音,一下一下,敲打在栖雀紧绷的神经上。
陆聿珩没有转身,也没有说话。他就那么站着,仿佛一尊静止的雕像,无形的压力却如同潮水般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充斥着整个空间,让栖雀几乎有些喘不过气。
她站在门边不远的地方,同样沉默着,垂着眼,目光落在脚下光可鉴人的深色大理石地板上,上面倒映出她有些模糊、微微颤抖的身影。她不知道他留她下来要做什么,也许是质问,也许是警告,也许……是更深的审视。她只能等,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徒。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被拉得无限漫长。窗外的天色,在夕照中渐渐暗淡,城市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勾勒出陆聿珩沉默的轮廓。他依旧没有转身,只是端起放在窗边小几上的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晃动,折射出冰冷的光。
就在栖雀几乎要被这令人窒息的沉默逼得想要开口打破时,陆聿珩终于动了。
他没有转身,只是对着窗外,淡淡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任何情绪:
“能源部长穆塔里,上任四个月,与当地三大能源家族联姻,废除前任补贴法案,推动新的《新能源投资保护条例》草案。草案核心,是强制要求外资控股超过30%的新能源项目,必须与本土企业合资,且本土企业占股不低于51%。”
他顿了顿,啜饮了一口杯中酒,语气依旧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这些信息,散见于过去三个月,十七家不同语种的国际财经媒体和当地政经网站的报道中,被提及的频率并不高,淹没在海量信息里。即便是陆氏的信息分析部,也是在三天前,才从一份长达两百页的深度国别风险报告中,提取出相关线索,并标注为‘高度关注’。”
他缓缓转过身,目光如寒潭深水,直直地看向她,那目光不再有会议室里的漠然,也不再是平日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一种穿透性的、仿佛要剥开她所有伪装的锐利探究。
“而你,”他放下酒杯,玻璃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而冰冷的一声响,“沈栖雀,一个自称只在父亲书房看过几本旧杂志,在纽约社区大学上过几门基础课,对金融‘一窍不通’的人——”
他朝她走近一步,高大的身影带着强烈的压迫感,将她完全笼罩在阴影之下。他微微俯身,目光锁住她因紧张而微微颤抖的睫毛,和那双努力保持平静、却依旧泄露出慌乱的眼睛。
“告诉我,”他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某种近乎危险的平静,“你是怎么在刚才那个会议上,在短短三十分钟的讨论中,仅仅凭‘道听途说’的几个字眼,就精准地捕捉到这位部长的背景复杂,以及他上台后政策转向这个,连专业团队都需要数天分析才能确认的、最关键的风险点的?”
他的问题,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她刚才在会议上那番“笨拙”回答下,隐藏的、近乎可怕的敏锐直觉和信息筛选能力。他不是在问她怎么看,而是在问她——你到底是谁?你的“无知”和“慌乱”之下,到底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东西?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只有远处传来的、隐约的城市喧嚣,和两人之间,那几乎凝滞的、无声对峙的张力。
栖雀的心脏,在那一瞬间,几乎停止了跳动。
(第十三章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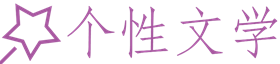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