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比记忆里更黑。
腐败的气味浓烈得像固体,堵在喉咙口。林川放轻呼吸,却觉得肺部运作吃力,吸入的每一口都带着陈年霉菌和某种更刺鼻的化学残留的味道。手电筒早就没电了,他只能依赖从坍塌处漏进的、极其微弱的天光,以及……他发现自己逐渐适应黑暗的眼睛。
瞳孔的浑浊似乎带来了某种补偿。阴影的层次变得分明,轮廓模糊的物体也能大致分辨形状。这是一种冰冷的馈赠。
他走到她曾经蜷缩的位置。地面潮湿,印着模糊的痕迹——不是鞋印,更像是……某种拖拽留下的水渍,已经半干。他蹲下,用手指抹了一下,凑到鼻尖。那丝甜腥的锈味,在这里变得明显了一些。
不是幻觉。
他心脏收紧,仔细查看周围。碎石、破烂的塑料布、几根枯骨(分不清是动物还是人类)。然后,在靠近内壁的缝隙里,他看到了一点反光。
小心翼翼地用刀尖拨弄,挑出一小片东西。不是玻璃,也不是金属。半透明,质地像干燥的胶质,边缘不规则。捏在指尖,冰凉,有韧性。他凑近闻了闻——正是那股气味最浓缩的来源。
这是什么?脱落的皮肤?某种分泌物?
他把这片东西用一小块布包好,塞进口袋。站起身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视野里的灰白噪点瞬间增多,像老式电视的雪花屏。他扶住冰冷的墙壁,闭眼喘息。
“饿……”
一个模糊的音节,不是出自他的喉咙,却仿佛直接响在脑髓深处。嘶哑,空洞,带着无尽的渴望。
林川猛地睁眼,四下环顾。隧道里只有他一个人。但那声音如此真切。
是外面的风声?还是……他自己的念头?
他用力甩头,试图驱散这不祥的幻听。手背上的痒感又来了,这次伴随着轻微的灼热。他看了一眼,昏暗光线下,那些细微的青灰色脉络似乎延伸了一点点,像扎根在皮下的丑陋根须。
不能久留。
他最后扫视了一圈这个令人不适的空间,正准备退出去,耳朵却捕捉到一丝异响。
很轻。悉悉索索。来自隧道更深处,那片完全被黑暗吞噬的区域。
不是风声。是某种……摩擦的声音。
林川僵住了。握枪的手渗出更多冷汗。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刻离开,好奇心(或者说,那种被无形线索牵引的感觉)却钉住了他的脚。
深处的黑暗里,有东西吗?是普通丧尸?还是……别的?
他侧耳倾听。摩擦声停了。接着,是一声极其微弱的、类似叹息的吐息。
“谁在那里?”林川压低声音问出口,立刻后悔了。暴露自己。
没有回答。
死寂重新降临,比之前更沉重。
走吧。快走。
他慢慢向入口后退,眼睛死死盯着黑暗深处。一步,两步。
就在他即将退到有微光的地方时——
黑暗里,两点微弱的、浑浊的惨白光芒,幽幽亮起。
是眼睛。
距离不远,大约十几米。
林川的呼吸骤停。他没有开枪,也没有动。那两点白光也没有移动,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
一种奇怪的、毛骨悚然的感觉顺着脊椎爬上来。那不是普通丧尸茫然而充满攻击性的“注视”。这目光里,似乎带着一种……观察的意味。
时间仿佛凝固。隧道口漏进的微光勾勒着林川紧绷的侧影,而深处的黑暗拥抱着那两点不祥的白芒。
然后,一个声音响起了。干涩,摩擦,音节扭曲,但勉强能辨认为语言。
“你……也……在……变……”
不是疑问,是陈述。
林川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它能说话?!它知道?!
“你是什么?”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
黑暗中的存在没有立刻回答。那两点白芒似乎眨动了一下(如果那算眨动的话)。悉悉索索的声音再次响起,像是它在调整姿势。
“离开……这里……”它说,每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出来,“‘他们’……会来……寻找……丢失的……”
“‘他们’?谁?丢失什么?”林川追问,向前微微挪了半步。
白芒骤然缩紧,显出一丝警惕甚至是……恐惧?
“走!”
这一次是短促的低吼。伴随着这声低吼,一股更浓烈的腐败气味扑来,其中混杂着与那片胶质物同源的甜腥锈味。悉索声变得急促,那两点白芒迅速向黑暗更深处退去,几秒钟后,彻底消失。
隧道重归寂静,仿佛刚才的对话只是一场过于逼真的噩梦。
林川站在原地,冷汗浸透了内衣。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得肋骨生疼。他慢慢退到入口的光亮处,才感觉重新夺回了呼吸的能力。
那个东西……它曾经是人。现在,它似乎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它知道自己在变异。它警告他离开。它提到了“他们”和“丢失的”。
“丢失的”……是指“她”吗?那个在猿馆哭泣、留下一滴冰冷眼泪的女人?
“他们”又是谁?其他像它一样的特殊感染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疑问像藤蔓一样缠紧了他的思绪,而身体内部那缓慢而坚定的变化,正一刻不停地提醒他:时间,可能不站在他这一边。
他最后看了一眼幽深的隧道,转身没入废墟渐沉的暮色中。
手背上的脉络,在暗淡光线下,仿佛又延伸了一毫米。视野边缘的灰白噪点,似乎也成了他世界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忽略。
而那声直接响在脑海的“饿”,在他走向下一个藏身处的路上,反复回荡,一次比一次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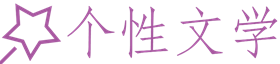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