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骼碎裂的清脆声响,在大殿中突兀地响起。
剧痛从下颌蔓延开来,几乎要将沈惊晚的意识吞没。
但她没有动。
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她只是看着他,用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
渊北寒眼中的黑色漩涡在疯狂搅动,几乎要将她整个人吸进去,碾成齑粉。
这个女人,死到临头,竟还敢用这种眼神看他。
杀意,攀升到了顶点。
只要他指尖再用一分力,眼前这个纤细的脖颈就会应声而断。
然而,那股毁灭一切的冲动,却在即将喷发的瞬间,被什么东西硬生生扼住了。
是她的眼神。
那里面没有恐惧,没有求饶,没有贪婪,甚至没有恨意。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纯粹的、死寂的平静。
仿佛他捏碎的不是她的骨头,而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
“咯咯……”
一阵低沉怪异的笑声,从渊北寒的喉咙深处滚了出来。
那笑声里,充满了压抑的疯狂和一丝……兴味。
他捏着她下巴的手,力道忽然一松。
虽然没有完全放开,却不再是那种欲要致人死地的钳制。
“有意思。”
他眼底的墨色漩涡渐渐平息,疯狂被一种猫捉老鼠般的玩味所取代。
“本座的命,就值一个入赘?”
他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带上了一丝戏谑。
瘫在地上的老管家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九千岁……笑了?
在这种煞毒攻心、杀戮满地的时刻,他竟然笑了?
沈惊晚感受着下颌上力道的减轻,神色没有半分变化。
“你的命,不值钱。”
清冷的声音,像是一盆冰水,兜头浇灭了渊北寒刚刚升起的那点兴味。
他的眸色再次沉了下来。
沈惊晚却仿佛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再次降临,继续说了下去。
“但你的权势,可以作为我复仇的刀。”
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掷地有声。
“这笔交易,你做不做?”
渊北寒没有立刻回答。
他只是盯着她,似乎想将她的灵魂从这具单薄的身体里看穿。
复仇?
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一个女人孤身闯入九千岁的府邸,用自己的命来赌一把看不见的刀?
沈惊晚迎着他的目光,再次开口,这一次,声音更轻,却仿佛一道惊雷在他耳边炸响。
“你体内的不是毒,是煞。源自你身上那件【万魂血煞铠】。”
“煞气日夜侵蚀你的经脉脏腑,腐蚀你的神智。陆百草的药只能压制,却不能根除。长此以往,药石无医,你最终会被煞气彻底吞噬,变成一具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
她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刺入渊北寒最深的秘密。
这些事,除了他和陆百草,天下再无第三人知晓。
她是如何知道的?
精准得……仿佛亲眼所见。
渊北寒眼中的玩味和戏谑,在这一刻,尽数褪去。
他彻底收起了所有的轻视。
这个女人,绝不简单。
她不是疯子,也不是单纯的寻死。
她是一把淬了剧毒的匕首,带着明确的目的,主动送到了他的面前。
大殿之内,再次陷入了死寂。
许久。
渊北寒终于松开了手。
他看着沈惊晚下颌上那片清晰的青紫指痕,眸色变幻不定。
“准了。”
两个字,从他口中沉沉吐出。
老管家闻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准……准了?
九千岁答应入赘了?!
然而,渊北寒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的心脏彻底停跳。
“整个天下,都给你当聘礼。”
那不是一句玩笑。
而是一个疯子,对另一个疯子许下的,最疯狂的承诺。
沈惊晚对这句石破天惊的话,没有表现出任何动容。
仿佛那所谓的天下,在她眼里,还不如一味珍稀的药材。
契约,口头达成。
她立刻转入正题。
“我需要一间药房,最好的药房。”
“从现在起,府中所有药材、器具,包括所有下人,都归我调遣,任何人不得有异议。”
她看着渊北寒,语气不是商量,而是命令。
“你需要绝对的安静,以及,绝对的配合。”
渊北寒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这个女人,给点颜色就开染坊。
刚拿到一点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发号施令了。
他没有说话,只是对着角落里已经吓傻的老管家,抬了抬下巴。
老管家一个激灵,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
“听……听姑娘的吩咐。”
“是,全听姑娘的吩咐!”
他现在看沈惊晚的眼神,已经从看一个死人,变成了看一尊活菩萨。
能压制住九千岁煞气的人,不管她要什么,都得给!
沈惊晚不再看渊北寒,转身走到一张还算完整的桌案前。
那上面,有刚刚被渊北寒打翻的笔墨纸砚。
她捡起一支狼毫,铺开一张染了血迹的宣纸,看都没看上面的污渍,提笔便写。
她的字迹,和她的人一样,清冷,锋利,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
“按方抓药,一刻钟内,送到净室。”
她将写好的药方递给老管家。
老管家颤抖着双手接过,只看了一眼,便愣住了。
上面写的,都是些最寻常的清心、静神的药材。
什么当归、川芎、白芍……
这些东西,能治九千岁的病?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抬头,想问,却对上了沈惊晚那双毫无情绪的眼睛。
所有疑问,瞬间被堵了回去。
“快去。”沈惊晚只说了两个字。
“是!是!老奴这就去!”
老管家不敢再有丝毫迟疑,揣着药方,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大殿中,又只剩下他们两人。
渊北寒靠坐在主位上,身上的煞气虽然被压制,但那股暴虐的冲动依旧在体内横冲直撞。
他看着沈惊晚的背影,看着她有条不紊地检查着殿内的狼藉,仿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这种感觉,很新奇。
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也从来没有人,能在他煞毒发作时,还敢站在他三步之内。
一刻钟后。
老管家带着几个下人,抬着一桶冒着热气的药汤,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千岁府最深处的净室。
药方上的药材,已经被熬煮成深褐色的药汁,一股浓郁的草药味弥漫开来。
沈惊晚走进净室。
这里是渊北寒平日里静修的地方,空旷,寂静,只有一个巨大的白玉池。
“把药汤倒进去。”她吩咐道。
下人们不敢怠慢,立刻将药汤尽数倒入池中。
白玉池的水,瞬间被染成了深褐色。
“你们都出去。”
“是。”
下人们如蒙大赦,躬身退下。
净室里,只剩下沈惊晚和渊北寒。
“脱衣服,进去。”
沈惊晚的声音依旧清冷,不带一丝波澜,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渊北寒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抬眸,看向沈惊晚。
那张脸上,没有半分女儿家的羞涩或扭捏,只有医者面对病患时的专注。
他突然觉得有些无趣。
他扯开衣袍,露出布满狰狞伤疤和诡异纹路的精壮上身,毫不避讳地走入白玉池中。
温热的药水瞬间包裹住他的身体。
一股清凉的气息,顺着四肢百骸的毛孔,缓缓渗入。
体内那股狂躁的冲撞,似乎被安抚了一些。
沈惊晚从袖中取出一个布包,摊开。
里面是长短不一,粗细各异的银针。
她走到池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闭上眼,凝神静气。”
渊北寒依言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他感觉到一丝尖锐的刺痛,从头顶百会穴传来。
紧接着,是风池、太阳、神庭……
一根根银针,被她精准而迅速地刺入他头部的各大穴位。
她的动作快而稳,没有丝毫犹豫。
随着银针的刺入,一股股清凉的气流,仿佛凭空出现,顺着穴位,涌入他的脑海。
那股盘踞在他识海之中,几乎要将他理智烧毁的狂暴煞气,像是遇到了克星一般,开始节节败退。
被砂纸磨过的喉咙,得到了滋润。
快要炸开的头颅,恢复了清明。
混沌的意识,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这种感觉……
太久违了。
久到他几乎忘了,一个正常人,该是如何思考的。
药浴的热力,与针灸的清凉,在他体内形成一种奇妙的平衡。
之前陆百草用药,只是强行镇压,如同筑起堤坝,洪水依旧在坝后咆哮。
而现在,沈惊晚的手段,却像是釜底抽薪,直接将那洪水的源头给掐断了一部分。
效果,立竿见影。
渊北寒缓缓睁开眼。
世界,在他的眼中,重新变得清晰。
他对她的医术,再无半分怀疑。
这个女人,真的有治好他的本事。
一炷香后,沈惊晚拔出了所有银针。
“今晚,你就睡在这里。”
她说完,转身便要离开。
“等等。”
渊北寒叫住了她。
他从池中站起,水珠顺着他肌理分明的身躯滑落。
他随手从旁边的架子上拿起一件外袍披上,然后从腰间解下一块木牌,丢了过去。
那是一块通体漆黑,不知是何木质的牌子,入手温润,上面用古篆刻着两个字。
北寒。
“见此牌如见本座。”
渊北寒的声音,恢复了几分属于九千岁的威严与低沉。
“从今日起,你就是这王府的女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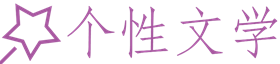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