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傍晚,小区广场上满是遛弯的人。陈悦推着老二的婴儿车,老大在旁边骑着小滑板车,像只快乐的小蝴蝶,绕着她转来转去。
“悦悦,又一个人带俩啊?”旁边带孙子的张阿姨凑过来,笑着搭话,“这俩孩子差得近,你可真能干。”
陈悦笑着帮老二调整了下遮阳帽:“没办法,孩子爸上班,只能自己带。”
“你婆婆呢?不来搭把手?”张阿姨嗓门大,旁边几个带孩子的老人也看了过来。
陈悦手里的婴儿车推杆顿了顿,随即笑了笑:“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帮不上。”
“嗨,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容易。”另一个阿姨接过话,“我家女儿也是,婆婆在老家,就我帮着带。说起来,就算不帮忙带,多少给点钱补贴补贴也行啊,俩孩子多费钱。”
这话像根细针,轻轻刺了一下。陈悦低头看着婴儿车里的老二,她正啃着自己的小拳头,吃得香呢。她笑了笑,没接话。
钱?刘姨不反过来从周叔那里拿钱就不错了。至于周叔,上次回去看他,他还抱怨说“这个月退休金刚到账,就被你刘姨取走大半”,陈悦没敢问是真是假,只当没听见。
老大骑着滑板车撞到了她的腿,奶声奶气地喊:“妈妈,抱抱。”
陈悦弯腰把他抱起来,小家伙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口水蹭了她一脸。她笑着擦掉,心里那点被刺到的不舒服,瞬间就散了。
晚上哄睡两个孩子,陈悦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想起大学时的日子。
那时候她在外地读大学,宿舍里四个姑娘,晚上躺在床上聊未来。轮到她时,她说“想找个相爱的人,结婚后有个温馨的小家,生两个孩子,婆婆能帮着带带,我和老公上班,周末一家人去公园,多好”。
那时候的憧憬,干净得像张白纸。她以为婚姻就是爱情的延续,以为婆媳关系只要“我对她好,她就会对我好”,以为日子就该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热热闹闹,和和美美。
可现实给她上了多么生动的一课啊。
婆婆不是亲妈,继母婆婆更是隔着一层。你掏心掏肺送的理疗仪,她可能转头就塞进柜子;你以为“以心换心”能处成母女,她却在背后算计着零花钱;你怀着孕操持过年,她连句问候都没有。
原来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的“期待”都能实现。社会这堂课,教她的不是“如何讨好”,而是“如何接受”——接受人性的复杂,接受关系的凉薄,接受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凑成“圆满”的样子。
“在想什么?”周明洗完澡出来,看见她对着窗户发呆。
陈悦转过头,笑了笑:“在想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觉得结婚过日子可简单了。”
周明走过来,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是我没让你过上你想要的日子。”
“别瞎说。”陈悦拍了拍他的手,“现在这样就挺好。你看,老大活泼,老二爱笑,你上班踏实,我在家带娃也安心。虽然累点,但心里不慌。”
是啊,心里不慌。
没有了对婆家的期待,就少了失望;放下了对“完美关系”的执念,就多了从容。她不再纠结刘姨为什么不帮忙,不再计较周叔为什么冷漠,那些人和事,就像小区里的背景音,听着就行,不用往心里去。
第二天早上,陈悦带着两个孩子在楼下吃早餐,张阿姨又过来了,手里拿着两个煮鸡蛋:“给孩子吃。”
“谢谢您张阿姨。”陈悦接过鸡蛋,笑着说。
“你说你这婆婆也是,就算不帮忙,好歹问问啊。”张阿姨又开始念叨,“我那亲家,虽然也不帮忙带,但每个月都给孩子寄奶粉钱,这才像回事。”
陈悦剥开鸡蛋,喂给老大一口,轻声说:“各家有各家的过法吧。我觉得吧,日子是自己的,好不好,自己知道就行。别人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强求不来。”
她的语气很平静,没有委屈,也没有抱怨。张阿姨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你说得对,是这个理。”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老二的小脸上,她闭着眼睛笑,露出没牙的牙龈。老大举着鸡蛋,追着一只小狗跑,笑声清脆。陈悦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
她想起刚结婚时,总觉得幸福是“婆婆帮忙带娃,自己光鲜上班,周末全家出游”的具象画面。可现在她懂了,幸福哪有那么多固定模式。
幸福是老大喊“妈妈”时,奶声奶气的依赖;是老二抓着她手指时,软软的温度;是周明下班回来,手里提着的那袋她爱吃的草莓;是自己拖着疲惫的身体,看着两个孩子熟睡的脸,心里涌上的那股“再累也值”的踏实。
社会这堂课,她或许曾经不及格,摔过跤,掉过泪,委屈过,崩溃过。但现在,她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答题方式——不苛责别人,不勉强自己,守好自己的小日子,一步一步往前走。
至于那些曾经憧憬过的“美好”,或许换了种模样,藏在柴米油盐里,藏在孩子的笑声里,藏在周明笨拙的关心和她日渐坚强的心里。
陈悦低头,在老二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轻声说:“咱们回家啦。”
推着婴儿车,牵着老大的手,一步步往家走。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稳稳地,落在地上。她知道,幸福或许会迟到,但只要不放弃,好好经营,它总会来的。而现在的每一步,都是在朝着它,慢慢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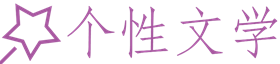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